文藝生活
黃土高原的褶皺里藏著歷史的年輪,路遙用鋼筆尖撬開這些溝壑時,滲出的不是墨汁,而是混雜著煤灰與麥芒的生命原漿。《平凡的世界》里沒有英雄史詩的鎏金封面,卻在鋤頭與鋼釬碰撞的火星中,鍛造出一部屬于普通人的青銅編年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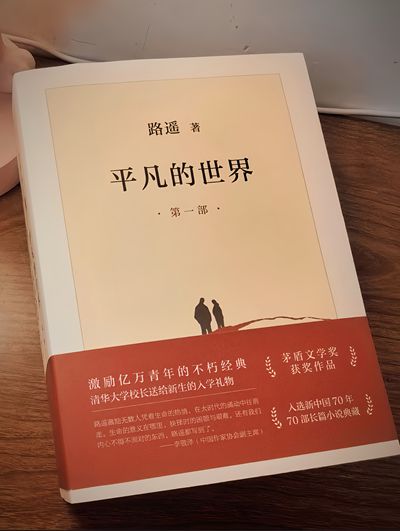
孫少安的膠鞋永遠沾著雙水村的泥,這抔黃土里拌著祖輩的骨灰與弟弟的遠方。開磚窯的火光中,我看見了農業(yè)文明向工業(yè)文明遷徙的剪影。他數磚坯時的神情,與父親孫玉厚撥算工分時如出一轍,只是算盤珠子上凝結的汗堿,變成了磚縫里滲出的現代化陣痛。這個被土地拴住雙腳的漢子,在磚窯騰起的黑煙里,完成了中國農民最悲壯的轉身——既要對抗饑餓年代的生存法則,又要迎接改革春風的凜冽。
金波的馬頭琴聲在青海草原被風吹散時,我聽見了工業(yè)化浪潮吞沒游牧文明的嗚咽。這個用軍用水壺裝烈酒的青年,把失戀的苦楚釀成了信天游,卻在裝滿瓷磚的卡車轟鳴中啞了嗓子。當他最終成為穿西裝的包工頭,那些曾經在月光下閃閃發(fā)亮的愛情,都變成了混凝土里的鋼筋骨架。
與哥哥相比,孫少平的世界更為遼闊。他穿著打補丁的褲子走進縣立中學那日,西北風正卷著1975年的政治標語呼嘯而過。他蹲在墻角吞咽高粱面饃的模樣,像極了那個時代所有蜷縮的青春。食堂泔水桶里漂浮的菜葉,宿舍床鋪下潮蟲啃噬的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,這些細碎如塵的日常里,卻蟄伏著覺醒的閃電。當他在破敗的縣圖書館翻開《紅與黑》,于連的野心與黃土高原的蒼涼在書頁間轟然對撞——知識這柄雙刃劍,既劈開了蒙昧的繭房,也劃開了理想與現實的鴻溝。
三十年后重讀這部百萬字巨著,突然在孫蘭香考入大學的段落里觸摸到路遙的溫柔伏筆。這個躲在磨坊寫作業(yè)的小姑娘,后來戴著校徽走進校園的身影,何嘗不是穿過了父兄用血汗?jié)茶T的橋梁?那些被生活反復揉搓的人們,在皺紋里刻下的不是滄桑的年輪,而是通往星空的等高線。
合上書頁時,工地上打樁機的轟鳴正震顫著城市的地基。恍惚間看見無數個孫少平從玻璃幕墻的倒影中走來,他們安全帽下的眼睛依然亮著煤油燈般的光。這部寫于三十年前的作品,至今仍在為我們這個急速膨脹的時代把脈——當物質的沙塵暴迷了雙眼,唯有那些在平凡中堅持仰望的人,才能在掌心養(yǎng)出不會干涸的月亮灣。(救援中心 孟梟)
編輯:達文娟


